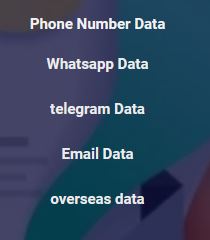古英语的句法,就像所有古日耳曼语的句法一样,几乎没有任何从属连词。故事是这样的:“……他们围攻了要塞,开始挨饿,他们进攻,逃跑,其中五十人死亡”(试着消除代词的歧义!)。 Þa肯定是一个标记,虽然几乎不是一种自发的“引起注意的手段”,将它与我们有害的like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我们的” like有时早在 18 世纪末就出现了,这一事实无关紧要。一切都有开始,但过去没有人说过:“他,就像,试图抢我的包,我,就像,尖叫。”
破洞牛仔裤:不符合我的品味有着令人惊讶的漫长进化史,它们仍然被视为现代语言的‘新兴’灾难性祸害?为什么‘ like ’是其中最严重的罪魁祸首?”(第 105 页)。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将忽略对令人惊讶的漫长进化史的提及):一个单独的粉刺(甚至可能很“可爱”)和皮疹之间是有区别的。事实上,如果约翰说:“我锻炼了大概十个小时”,那没问题:让他说吧。但量变变成了质:like充斥了我们的语言,不再意味着“大约”。作者的以下陈述尤其具有特色:“这种非标准的‘ like’用法似乎是人们最难接受的,这很不幸,因为它是英语中扩展最快的用法”(第 114 页)。我不这么认为。毫无疑问,绰号f—ing是英语中扩展最快的,动词f—up也是如此。那又怎么样?我们应该拥抱它们吗?
弗里德兰没有提到这个被称为语言现象再生的过程。它甚至发生在语音学中,但更常见于语法中,即“进行时”形式让位于曾经被丢弃的形式(这曾经发生过在变音符号的历史和动词变位中,尽管英语中没有发生过)。like 的寿命是无法预测的。几十年前,主要的填充词是you know,弗里德兰只是顺便提到了它。我记得一位博士生的演讲中you know占据了一半的时间。这个话语标记、情节增稠剂 菲律宾电报数据库 和语言聚焦器现在在哪里?消失了或者几乎消失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形容词cool征服了世界(其已不复存在的前身是groovy)。它还没有完全消亡,但肯定不是形容词世界的最前沿。
奥尔德斯·赫胥黎,一位高雅人士
。维基共享资源(公共领域)
在语法中,流行用法几乎总是胜出。第三人称单数“speaketh”已不复存在。四个世纪前,“speaks”、“says”等是北方的粗俗语,莎士比亚只允许福斯塔夫的闺蜜同伴使用它。现在这是标准英语。其他语法形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不稳定。例如,美式英语很久以前就失去了“whom”形式。所谓的规范试图重新安装它,但结果却很糟糕。这里有两个来自可靠来源的最近的例子:“视频显示警察追捕嫌疑人,警方报告称他在几分钟内被拘留”和“这对产科医生来说也是如此,我相信他们总体上是最有同情心的医生之一。”但这种寄生虫不是语法。它是“用法”:它来了,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消失。
我认为弗里德兰在整本书中只提到过一次“文化”这个词,但语言除了是一种交流手段之外,难道不也是一种文化工具吗?大多数文化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都具有符号价值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穿破洞牛仔裤,因为这种牛仔裤“会一直存在”,就像据称的“像”(第 100 页;说的是“像”,而不是“牛仔裤”)。奥尔德斯·赫胥黎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是高雅文化”的文章,以回应一篇题为“我是低俗文化”的文章。我站在赫胥黎一边。我非常乐于穿着做工精良的衣服,享受我们最优秀作家的丰富词汇。我绝不会强迫任何人接受我的品味,但我讨厌像和你知道的这样的填充词, 虽然我知道最低级的文化形式通常像杂草一样占上风,但我至少不会急于为它们的胜利做出贡献。
如果这个话题引起了你的兴趣,我可能会在下周继续同样的讨论。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