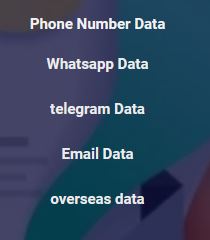萨曼莎·史密斯:是的。我认为答案有两个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被强行推入这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从一个公共平台,只关注安德鲁作为一名篮球运动员,而我的角色是支持他。然后,我变成了安德鲁的照顾者,一个病人,陪伴他度过病痛。现在,这个平台变成了:“好吧,那么萨姆是谁?萨曼莎·史密斯是谁?”我认为这是最艰难的转变:现在这个平台不再被分享,感觉你拥有这个平台的理由已经荡然无存。所以,你会问:“那又怎样?”
但我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困境中依然坚持分享,因,我们一生都渴望被利用,从约会到婚姻,当然,我们从未想过最终会变成这样。我不是说上帝让安德鲁患上了癌症。我完全不相信。只是我们一直渴望被利用。我们一直渴望成为积极的影响——成为优雅行事、帮助他人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我想,这就是那种感觉:即使我的处境变了,我的目标却始终如一。所以,我当然想继续这段对话,无论境遇如何翻天覆地。
乔:哇哦。非常感谢你分享这些。
关于情节转向公开演讲……
乔:现在,公开演讲是你唯一的职责吗?除此之外,你还做其他项目吗?
萨曼莎·史密斯:公开演讲,并尝试更多地涉足咨询领域,我想这 马其顿电报号码数据库 只是小规模的公开演讲。但话说回来,这只是一种对他人生活的探讨,这正是我内心的所在。这主要通过公开演讲来实现,但也通过咨询和写作来实现。我做了很多写作,试图再次找到那个最佳状态,这很困难。尤其是在安德鲁去世后,当我努力克服悲伤时,我经常会问自己“现在该怎么办?”之类的问题。
我遇到安德鲁的时候……天哪,14岁。当时我还是个婴儿,还是个孩子。人生规划几乎都围绕着安德鲁,或者说,安德鲁就在其中。你知道,我的计划是去海外打五年篮球,生四个孩子,待在家里照顾他们,养育他们,爱护他们。这就是我的计划。所以,当你预想的未来不再可能,你真的会陷入那种“哦,糟糕,现在怎么办?”的恐慌状态,几乎是。我现在还在纠结“现在怎么办?”
即使这项事业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我仍然会时不时地问自己:“这样可以吗?”因为这不是我真正想过会做的事情。当进展稍慢一些时,我也不会灰心丧气,想着:“也许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我觉得很容易陷入“也许这不对”这种想法。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克服它。我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
乔:当然了。这太难了。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萨曼莎·史密斯:我甚至都没完成。我最初从事新闻工作,但很快意识到那不是我喜欢的写作领域。它根本不适合我。所以,我最终转向了心理学,并试图一点点地学习。但话说回来,我当时的想法根本不是利用这个学位,因为我希望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我更希望能够拓展我参与志愿服务和帮助他人的方式。这可以说是我的最终目标。后来我的想法是,当我们在海外时,我会一点点地完成它,并在网上完成它。那本来是我在海外期间的项目。但后来,显然,安德鲁生病了,这件事就被搁置了。
乔:这很有意思。那么,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公开演讲的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开演讲是一件令人畏惧的事情,所以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萨曼莎·史密斯:公开演讲对我来说一直都很自在。它从未让我感到紧张。而且,我和安德鲁经常一起公开演讲——一开始是作为篮球运动员,后来他生病了,我们也会分享彼此的心路历程等等。所以对我来说,公开演讲一直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但我确实记得那个确切的时刻,几乎可以说是“啊哈”的时刻。当时我在巴特勒大学参加一个演讲活动,和另一位演讲者一起发言。我记得当时在那里,演讲的主题是赋权年轻女孩,对抗攀比,以及我们作为女性——作为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但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感觉就像:A)这是安德鲁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到快乐;B)我可以永远做下去。真的,我可以永远做下去。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活着,仿佛被滋养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你知道,我想再多探索一下;我想看看这里是否有我深入其中的空间。”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可以永远做下去”。然后,我又开始想,“好吧,那我们就试着永远做下去。”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