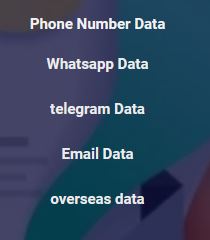的言论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保护仇恨言论,迫使少数群体为其参与公共生活寻找理由。学生们认识到,如果仇恨言论是我们为言论自由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笔代价中的大部分将由少数群体和女性承担。因此,当有发言者质疑某个群体的生存权利时,大学应该划清界限。整个学术界都应该反对这种言论,就像它经常反对谎言和既定观念一样,因为故意制造的谎言(现在被称为“深度造假”)会破坏我们确定真相的能力。 社交媒体上关于政治广告的争论 表明,如果深度造假是我们为言论自由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笔代价中的大部分将由那些资源较少的人承担。
如果从平等的角度而非冒犯的情绪或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模糊术语来看待校园争议,就会发现大学和社会 丹麦电报数据库 中自由与平等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言论自由只是一项空洞的承诺,因为它只赋予那些拥有权力、资源和社会地位的人,目的是剥夺其他人的生存权。
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和芝加哥大学的指导方针旨在结束校园争议,这些争议是关于参与平等以及大学不重启长期争论的特权的斗争。当大学偏袒空洞的言论自由概念或将言论作为其 存在的理由时,它们就损害了其保证所有合格学生和教师平等参与的法律义务。它们还放弃了作为真理仲裁者的角色,言论自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其促进知识发展的目的所必需的和为其服务。
校园争议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它们表明,言论自由一旦沦为空洞概念,就会被用来对抗民主制度和大学本应服务的使命。1949 年,美国最高法院 法官罗伯特·杰克逊 在 特米尼耶洛诉芝加哥案中警告称,宪法绝不能成为“自杀协议”。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发现的那样,对仇恨言论和深度造假的全面辩护,可能会破坏而不是保护民主。
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担心,今天对仇恨言论的任何管制都会导致明天对异议的管制。另一些人认为,接触仇恨言论可以培养坚韧的品格,如果学生在田园诗般的校园里免受种族主义的侵害,他们将无法为现实生活做好准备。但正如滑坡并非不可避免一样,没有证据表明仇恨言论可以塑造性格。然而,有证据表明,仇恨可能导致谋杀,例如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挪威奥斯陆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等地。在我们这个仇恨只需点击一下按钮就能传播的时代,一个地方的僵化言论绝对主义可能会导致很远的地方的死亡。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允许言论,让人们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不能把言论自由变成一种僵化的虔诚,让一些人剥夺其他人的这种权利。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